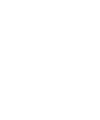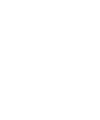醉时·春拂柳 - 47:贪生怕死的蠢货,不如宥儿
周娉婵斜倚在贵妃榻上,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叩着紫檀木的榻沿。漱玉宫内静得骇人,唯有鎏金狻猊炉口中吐出的缕缕白檀香,盘绕升腾,氤氲了她半张明艳却隐含戾气的脸。窗外暮色渐合,将最后一点天光也吞噬殆尽,宫人早已悄无声息地点亮了宫灯,暖黄的光晕落在她身披的白狐裘上,却化不开那通体透出的寒意。
掌事嬷嬷容娟垂手立在下首,声音压得极低,一字一句,将宫外刚刚探得的、关于楼家与崔家可能被赐婚的消息禀报上来。话音落下许久,周娉婵都未置一词,只那叩击榻沿的指尖,节奏愈发急促,透露出主人翻江倒海的心绪。
“咯”的一声脆响,她终于停了动作,染着蔻丹的指甲在木料上划出一道浅痕。“当真?”她开口,声线依旧慵懒,却像绷紧的弓弦,藏着危险的张力。
“千真万确,娘娘。虽未明发谕旨,但……风声已透了出来,怕是八九不离十了。”
容娟头垂得更低。
“哼,”周娉婵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冷笑,猛地从榻上坐直身子,那件价值连城的白狐裘顺势滑落,她也浑然不顾,“楼巍……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!”女人倏地起身,赤足踏在铺满地毯的冰凉的金砖地上,来回踱步,裙裾曳地时发出的沙沙的声响,在这过分寂静的殿宇内,显得格外刺耳。“即便是要赐婚,圣上为何按下不表?秘而不宣,莫非……其中还有别的打算?”
周娉婵越想,眉头蹙得越紧,几乎拧成一个结。
前几日,她刚费尽心思说服了谢惟渝去争一争这婚事,指望着他能借此在陛下面前露脸,压过东宫一头。谁知今日,便传来这等消息!楼家本就是东宫的铁杆支持者,若再让他们与平原侯府同苑文俪通过这桩婚事连成一气,势力必将如虎添翼。
那东宫里的病秧子,本就占着嫡长的名分,若再得此强援,岂不是……岂不是要稳坐钓鱼台,再难撼动?
一股邪火猛地窜上心头,烧得女人五脏六腑都灼痛起来。周娉婵骤然停步,目光锐利如刀,刺向窗外黑沉沉的夜空,仿佛能穿透宫墙,看到东宫那一片碍眼的殿宇。
“一个靠着汤药吊命的短命鬼!凭什么……凭什么同我的宥儿争!”这句话几乎是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带着浓烈的嫉恨与不甘,在空阔的殿内显得异常清晰。
“娘娘!慎言!”容娟脸色骤变,也顾不得尊卑,急步上前,声音压得几乎只剩气音,“隔墙有耳啊!这皇宫说到底,是皇上的皇宫,处处……处处皆是陛下的耳目!”
周娉婵胸口剧烈起伏,显然怒气未平,但容娟那句“陛下的耳目”像一盆冰水,让她稍稍冷静了些。女人深吸一口气,强迫自己压下那几乎要破体而出的怨毒。
容娟见她神色稍缓,才继续低声道:“万幸,万幸三殿下昨日已奉旨动身,前往漠安处理鼠疫赈灾事宜。这一来一回,至少需要十日功夫。殿下离宫前也与圣上奏明,待漠安事毕,便可直接转道南塘庆贺郡主生辰……娘娘,眼下我们切莫自乱阵脚。
既然圣旨还未明发,一切就尚有转圜之机。即便……即便最终定下,相信三殿下心中也自有考量谋断。当务之急,是娘娘您要稳住心神,静观其变。”
周娉婵沉默地听着,缓缓走回榻边,却没有坐下。女人伸手,指尖掠过那件滑落的狐裘,一下下的抚摸着,良久,她才幽幽叹出一口气。
“罢了……本宫知道了。”
周娉婵终于重新裹紧了那袭白狐裘,柔软的毛锋拂过下颌,带来一丝虚假的暖意。她缓缓坐回榻上,脊背挺得笔直,下颌微抬,那股惯常的、无可指摘的雍容高华气度,重新回到了她的眉宇之间。仿佛方才那一瞬间的失态与厉色,不过是灯影造成的错觉。
女人指尖漫不经心地捻着狐裘边缘一根格外莹润的毫毛,声音放得轻缓,却字字清晰:
“这盘棋,既然开了局,自然要看下去。本宫……只是有些忧心宥儿。”
她话语微顿,目光悠悠飘向殿外沉沉的夜色,似叹似诉,尾音融进冰凉的空气里,泛起一丝恰到好处的、属于母亲的涩然:
“你也知道,这孩子从小便最是懂事,最让人省心,却也……最教我心疼。他何曾像别的皇子公主那般,撒泼打滚地要过什么?即便是为了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,也是本宫,还有周家,在背后推着他、乃至逼着他,一步一步往前争。他自个儿心里,何曾真正炽烈地、不顾一切地渴求过什么身外之物?”
“可这一次,不同了。” 周娉婵的指尖蓦然停下,那根捻了许久的雪白毫毛,自她指间无声滑落,飘摇着坠入光影朦胧处,了无痕迹。“他提起元徵那孩子时的神情,本宫是瞧在眼里的。那点儿光亮,藏不住,也做不得假。”
周娉婵缓缓吁出一口气,仿佛真被那一点「光亮」触动了心肠,“本宫这个做娘的,冷眼看了这许多年,算计了这许多年,倒也是头一回……生出几分真心,想成全他一回。”
她抬起眼,目光落向始终垂首侍立的容娟。殿内烛火在她眼中跃动,将那深藏的、冰冷的算计,巧妙地掩映在一层温情的薄雾之后,真意假意,虚实难辨:
“皇位,自然是要争的。那是命,是运,更是不得不走的路。可若是在这条荆棘路上,也能让他得偿所愿,娶一个自己真心悦慕、放在心尖上的女子,岂不是两全其美?”
周娉婵话音渐低,染上一抹清晰的忧惧与疼惜,“本宫只怕……只怕这突如其来的赐婚,若真成了定局,会生生伤了他的心。我与他父皇……这些年,已经伤他够深了。这一回,我是真的盼着他能畅怀,能快活些。”
她停顿片刻,声音压得更低,像是自语,又像是寻求一种残酷的慰藉:
“哪怕……哪怕元徵那孩子寿数有限,是个朝不保夕的身子。可若能陪他几年,暖他几年,在他最艰难的时候,予他几分真心的慰藉……不也好么?总好过,让他什么都得不到,什么都留不住。”
这番话,她说得情意恳切,宛如一个纯粹为儿子终身幸福计量的慈母。可那「陪他几年」、「慰藉」之语,却也冰冷地道出了崔元徵在她眼中,终究只是一件可以计量时效、用以抚慰儿子的“器物”。
温情与利用,真心与算计,在她这里早已缠绞成一团解不开的乱麻,连她自己,或许也分不清哪一句是纯粹,哪一句是伪装了,可偌大的殿宇里,又何止她一人看不清,只怕坐在宝座上那位也不曾看清过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
“陛下,已按照您安排的,将消息漏给了崔大人、贵妃娘娘,还有……”
谢重胤端坐于御案之后,指尖搭在书页边缘,许久未曾翻动一页。御书房内烛火通明,将他半边脸庞映得清晰,另半边却隐在书架投下的厚重阴影里,看不出喜怒。
掌事太监张泉垂首跪在冰凉的金砖地上,已有一炷香的时间。
他将头埋得极低,额头几乎要触到地面,用那特有的、不高不低、恰好能让御座上的人听清,却又不会惊扰这满室沉寂的嗓音,一五一十地禀报着消息是如何「不经意」地透给了崔愍琰,又是如何借着宫女们的闲话,悄无声息地流进了漱玉宫周贵妃的耳朵里。
他语速平稳,措辞精炼,每一个字都像是斟酌过无数次,确保既陈述了事实,又不掺杂任何多余的猜测。
谢重胤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,仿佛张泉禀报的不过是今日御膳房的点心单子。他甚至又翻过一页书,目光落在密密麻麻的字迹上,似乎看得专注。只有偶尔掠过烛火时,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会极快地闪过一点寒光,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。
直到张泉最后一个字音落下,御书房内重归死寂,只余烛芯偶尔爆开的轻微“噼啪”声。谢重胤这才缓缓将书册合上,随手置于案头。男的抬起手,用修长的指节揉了揉眉心,动作间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,但当他开口时,声音却平稳得听不出丝毫波澜,像是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水:
“东宫……有动静吗?”
这句话问得极轻,却像一块烧红的铁钎,猝然烙在张泉的心头。他伏在地上的身躯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,帝王看似随意的垂询,往往正是最危险的试探。御书房内空气凝滞,连龙涎香缠绕的轨迹都仿佛慢了下来。张泉将头埋得更深些,额际触着冰凉的金砖,迅速在脑中筛过今日东宫线报的每一个字眼,权衡着轻重,拿捏着分寸。
片刻沉吟后,张泉才谨慎地开口,声音平稳依旧,却字字清晰:
“回陛下,东宫今日……又召了那位青玄真人入内。闭门约一个时辰,据报,所言仍不离……炼丹、辟谷,与长生久视之法。”
“长生?”
御座之上,谢重胤终于有了点不同的反应。他鼻腔里逸出一声极轻的、几乎听不真切的嗤笑,像是听见了什么荒唐透顶的笑话。搁下手中一直虚握的玉石镇纸,男人身体微微后靠,隐入高背御座更深的阴影里,唯有那双眼睛,在烛火映照下,锐利得惊人。
“呵……长生?”
谢重胤又重复了一遍,语气平淡,可那平淡之下,却翻涌着足以冻结血液的寒意与无边的讥诮。男人目光掠过御案上堆积如山的、关乎旱涝、边关、赋税的奏折,又仿佛穿透重重宫墙,看到了东宫里那个沉溺于虚幻长生梦的储君。
“蠢货。”
薄唇轻启,两个字,冰冷地掷了出来。
没有雷霆之怒,没有痛心疾首,只有一种极致淡漠的、近乎俯视的评价。
“贪生怕死的蠢物。”
谢重胤薄唇间碾出的这六字,裹着浸骨的寒意与毫不掩饰的轻蔑。他目光掠过虚空,仿佛已穿透宫墙,看见东宫之内焚香缭绕、丹炉赤红的荒唐景象。
“到底不如宥儿。”
提及谢惟渝时,谢重胤眼底那层严冰般的冷峭,几不可察地化开了一丝极细微的裂隙,泄出些许近乎欣赏的微光,虽转瞬即逝,却已足够让久伴君侧的张泉捕捉到那微妙的不同。那并非普通的父子之情,而是一位帝王对一把锋利、趁手且忠诚的武器的认可。
“他眼里,”谢重胤的视线落回御案上摊开的、来自漠安疫区的加急奏报,语气里的讥诮转化为一种沉重的冷然,“只剩下那点虚幻的丹砂火候,斤斤计较于铅汞配比,做着霞举飞升的大梦。却对门外真实存在的江山万里、民生多艰,视而不见,充耳不闻。”
男人指尖点在那份奏报“饥民待哺,疫病蔓延”的字样上,声调依旧平稳,却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钉子,砸在寂静的空气里:
“朕给他储君之位,予他观政之权,是望他体察黎庶之苦,历练治国之能。而他……却将心思、将时辰,虚耗在这些方士蛊惑的妄念之中。如此心性,如此眼界——”
谢重胤没有说完,只极缓地摇了摇头。那未尽的言语比任何疾言厉色的斥责都更具否定之意。一个宁可沉溺于虚幻长生,也不敢直面天下重任,更无魄力承担生老病死的储君,在他心中,已然与“不堪大任”画上了等号。
与之相对的,是谢惟渝奉命前往漠安时,那毫不犹豫领命、甚至主动提出深入疫区巡查的担当。两相对照,云泥立判。这份赞赏未曾宣之于口,却已在这冰冷的对比与那声“不如宥儿”的定论中,显露无遗。
顿了顿,谢重胤指尖在光滑的御案边缘轻轻一敲,发出一声清脆的微响。
“张泉。”
“奴才在。”
“东宫用度,尤其是涉及丹药、方士的支取,从今日起,着人细细记档。一应进出人物,给朕盯紧了。”
谢重胤的语气恢复了平静,仿佛刚才那冰冷的“蠢货”二字从未出口,“至于那位青玄真人……既如此热衷长生之道,便让他好生为太子‘炼丹’。所需‘药材’,不必吝啬,尽可从内库拨给,务求……精益求精。”
张泉心头一凛,立刻明白了话中深意。陛下这是要纵着东宫,让那方士“尽心尽力”地炼丹,同时将一切记录在案。这已不仅是监视,更是……为将来可能的需要,备下无可辩驳的实证。他不敢有丝毫迟疑,立刻应道:
“奴才遵旨。定会安排妥当,绝无疏漏。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