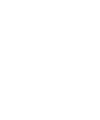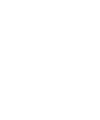情迷1942(二战德国) - 重返石头大宅
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。就算住进去呢?未来又能如何?住进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,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地等待着巴黎变天吗?
她慢慢睁开眼,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。影子里的女孩脸色惨白,眼圈微红,可她偏偏看见,那双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在破土而出,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
不能再这样了。
她需要一条路——一条自己能走的路,不是十天之后的未知,不是任人摆布,是此刻就能迈出的第一步。
俞琬拉开书桌最底层的抽屉,叔叔最近的一封信,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了。
她前天已经去过电报局了。窗口的女职员机械地重复着:“特殊时期,国际电报需要审查。发往中立国的,需三到五周才能送达。确认要发吗?”
她当时心就凉了半截,可人已经站在那儿了,还是咬着牙付了钱,发出简短的一句话。
但她心里清楚,现在,连电报的送达都要以“周”为单位算,那些寻常的邮路,怕是早就断得无影无踪了。
思绪纷乱间,她忽然想起每周三准时来收医疗废物的老约瑟夫,那个法国老人最喜欢喝她泡的热姜茶。有次闲聊时,倒偷偷和她提过,他儿子“在瑞士边境做些小生意,有时候也帮人捎些...特别的东西。”
或许……或许能托他带个信?这几乎是她能想到的,最快的渠道了。
钢笔悬在信纸上,她想写:“巴黎危急,需紧急撤离路径。”
可笔尖却迟迟没落下去。最终,她颓然把脸埋进掌心里,肩膀垮了下来。
太慢了。
现在整个法国的交通都近乎瘫痪,铁路被军事管制,公路关卡林立。就算老约瑟夫的儿子真能把信送到瑞士边境;就算叔叔能立刻调动所有关系,为她开出一条通道来,这前前后后加起来,乐观看也得差不多两周了。
两周后,巴黎是什么样子?盟军的炮火会不会已经推进到塞纳河畔了?更别说,如果信还没过边境,就被搜查截获呢?
女孩放下笔,就在这时,另一个名字浮现在脑海里——朱会长。
唐人街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,假证件、藏身所、地下交通线他们都有。他应该会帮忙的。
她攥了攥小手,又从抽屉里翻出另一样东西来,半盒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药片。在如今的巴黎黑市,它算得上硬通货,足够换两条香烟和足足三公斤的黄油了。
可光是阿司匹林作为谢礼怕是还不够,她手头还有一对珍珠耳环,是克莱恩送的。
手指刚触到微凉的珍珠上,又慢慢放了下来。
人情债用一次就薄一次。她已经厚着脸皮去求过朱会长两次了,两次他们都为她担了不小的风险,再去找他,她实在有些开不了口。
朱会长或许能帮她藏起来,甚至能弄到去马赛或尼斯的证件,混进南下逃难的人流里。可每向南一步,就离克莱恩远一程。
她仿佛看见地图上那道不断拉长的红线,从马赛到尼斯,再到西班牙边境,最终将她和他,隔成了两个再也无法触碰的世界。
只这么一想,心就被狠狠攥了一下。
她摇摇头。这条路,暂时放在最后吧,如果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再考虑南下的事。
不知不觉间,天色已经全黑了,街灯一盏接一盏亮起,晕开一团团孤零零的光晕。两条路明明白白地摊在眼前,却像是两道看不到尽头的岔路口,一条太慢,也太险;另一条……却太远了。
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,再有一个小时,宵禁的钟声就要敲响了。
此刻,一个画面不期然闯入到脑海里来。
是克莱恩离开巴黎前的那一夜,福煦大道官邸的书房里。他坐在沙发上,她依偎在他怀里,谁都不愿提起即将到来的分别。房间里很暖,暖得让人昏昏欲睡的,他的心跳声透过衬衫传到她耳边,像沉稳的钟摆似的。
时间像是被蜂蜜给粘住了。
在她眼皮开始发沉的时候,他的声音才在头顶响起。
“……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无法挽回,”他微微动了动,转过她身子,让她直视着他的湖蓝色眼睛,“你找不到我,也等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。”
“就回这里来,打开书房东墙书柜后的保险柜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“密码是你的生日,倒过来写。”他捧起她的脸,拇指一遍遍抚过她脸颊,她从未见过这样的克莱恩——素来冷静自持的眼里,竟翻涌着一种她读不懂的、近乎悲怆的认真。
“可是你说过,如果……我可以去找……”
“那是在一切还能按计划进行的情况下。”他打断她,呼吸扑在她额前,那个吻落下来时,她尝到了他唇间威士忌的微涩。“但战争,从不按任何人的计划进行。答应我,如果真到了那一天,不要犹豫。”
俞琬记得自己当时懵懂又心慌地点了点头,第二天他就走了,她也把那几句话,连同那个夜晚的温暖一起,锁进了记忆深处去。直到此刻。
她猛地转身,抓起衣架上的外套。
去那个地方,那个曾经被他们短暂地称为“家”的地方。
搭着最后一班电车到那里时,天空已经墨一般黑了,那座被遗忘的石头大宅还静静卧在林荫道上。德军征用的建筑大多有卫兵把守,但这儿是克莱恩的私宅,他走后只留了一个人看着。
走近了看,那卫兵已经是新面孔,瘦瘦小小,看着顶多不过十四五岁。那男孩看到她从夜雾里走过来,整个人猛地弹起来,眼睛瞪得溜圆,跟见了鬼似的。
原来,老的那个一个月前也被调去东线补空缺了,眼前这孩子,自我介绍时还磕磕绊绊的,说之前在慕尼黑读中学。
她用钥匙打开侧门,打开灯,慢慢走进去。
玄关、旋转楼梯、铺着波斯地毯的走廊…… 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,一切都还在,一切又都不一样了。
时间仿佛凝固在了他离开的那一天,又仿佛以另一种方式流逝着。
那架三角钢琴的琴盖还开着,上面落了薄薄一层灰,她轻轻按下中央C键,消音的琴槌只发出沉闷的叩击,可记忆里的《爱之梦》却瞬时苏醒开来——
那时候,他们挤在这张琴凳上,四手联弹李斯特的曲子,她的指下流淌着跳跃的旋律,他的节奏稳稳托住旋律的根基。
弹到兴头上,他会故意使坏,冷不丁转入巴赫的赋格,严谨的复调如蛛网缠住她的主旋律。“赫尔曼!”她笑着捶他肩膀,他趁机将她搂得更紧,两人的手在琴键上撞出一串尖锐的不协和音,像童年时故意踩响满地的落叶那样。
那钢琴,大多数时间是她在弹。
但也有时候,是克莱恩坐在那,弹奏一首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那时,他脸上所有属于军官的冷峻都会软化下来,琴声如水,漫过地板,漫过窗棂,浸满整个房间,也浸到她心里去。
所有记忆一股脑奔涌过来,冲得她眼眶发热。
餐厅里,那张能坐下十二个人的长条餐桌也空荡荡的。
她记得他们曾在这里消磨过无数个黄昏与清晨。有时是她下厨做的番茄炒蛋,有时是他从军官俱乐部“顺”回来的巴伐利亚白香肠。
他总是吃得很快,风卷残云,说在军营习惯了。她就故意把饭粒数着吃,细嚼慢咽的。直到他无奈放下刀叉,靠在椅背上,蓝眼睛里漾着笑,听她说诊所里新收治的那只跛脚流浪猫,又或是抱怨隔壁那位总忘记复诊吃药的老太太。
现在这里,只余下灰尘的味道了。
她几乎小跑着逃离餐厅,噔噔噔地冲上二楼。
主卧室的门虚掩着,她轻轻推开。床铺得整整齐齐,和他离开时那样半点没变。床头柜上,静静躺着海涅的《歌集》,书签夹在他们一起读过的那页。
她走过去,颤抖着拿起它。
她记得很多个夜晚,她睡不着,他就把她圈在怀里,用低沉的普鲁士腔,给她讲他小时候在勃兰登堡森林里打猎的故事,他的手掌很大,很暖,能完全包住她的手。
他也会给她读诗。
有时读着读着,声音会突然慢下来,哑下来。书被搁到一边,他的吻落在她的额头、鼻尖,最后是嘴唇,交换的气息间全是雪松的味道。
空气渐渐变得稀薄而滚烫,他的衬衫扣子不知何时被崩开,露出坚实的胸膛来,她的丝质睡裙也被褪到了脚踝去。
然后是脸红耳热的喘息,汗水交织的相拥,攀至顶峰时的眩晕与战栗…..当一切回归平静,他总会把她牢牢圈在怀里,下巴抵着她发顶,直到她沉入梦乡去。
还有那个周末的清晨,她记得清楚,阳光透过窗帘缝调皮地洒进来,她被扰得先醒了,懒懒靠在床头翻书。
身旁的人动了动,长臂一伸把她捞回怀里去,温热的唇擦过她颈侧敏感的肌肤,嗓音沙沙震着她耳膜:“念给我听……”
她便红着脸念里尔克的句子:“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,无缘无故在世上哭,在哭我……”话音未落,他闭着眼笑,手臂却收紧几分:“不许哭。我在这里。”
我在这里….
鼻尖的酸意再也抑制不住,她用力眨眨眼,花了好长时间,才把那片湿热的雾气生生压回去。不能哭,现在不是时候。
书房在走廊尽头。
她走向那排顶天立地的橡木书柜,按照克莱恩说的,抽出那本浅蓝色封皮的《战争论》,指尖触了触里面的木质暗格,整个书柜便缓缓向侧面滑开半米,露出一个保险柜来。
密码她记得的,是她的生日倒过来,民国九年九月二十七日。带着点德国人特有的严谨,他还特意记在小本子上,Geburtstag: 09.09.27,当时她看到还笑问,用这个会不会太容易被人猜到。
“除了你,没人会来这里。”他这么答。
手指转动密码盘一圈又一圈。最后一个数字对准刻度时,咔哒一声闷响,金属门弹开了。
暗格并不大,里面只放着一个深蓝色的天鹅绒盒子。她把它拿出来,手指不禁有些发颤。
盒子里有几张纸。最上面是一张船票,巴黎到里斯本,波塞冬号头等舱,只是日期栏是空白的。
下面压着一张特别通行证,纸面已经有些微微卷曲了。权限栏里标注着可以穿越所有占领区边境,而有效期那一行,填的是1945年12月31日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